估量阅读韶光18分钟
2019年2月中旬

倒春寒袭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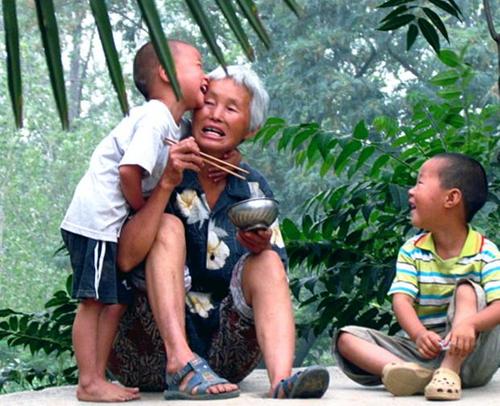
那晚我们结束加班
从温暖的办公室来到室外
觉得就像衣服被拔光了一样平常
八点多的科华路行人匆匆
年轻人要么在路边瑟瑟打车
要么钻进便利店享一时安稳
我们走上天桥
想去寻家面店对付一顿儿
寒风中天桥那端亮着微弱的灯光
两个婆婆正守着他们油纸铺就的杂货摊儿
天哪寒风中的婆婆好可怜我们感叹
这个选题在我们单方面的怜悯中出身
我们想走遍成都
去记录这些婆婆背后的心伤和困难
意外的是
我们以科华路为出发点
走到西门的清江路南门的玉林横街
北门的万福桥东门的双桥子
我们所遇见和寻到的婆婆
没有一位通报出悲苦和艰辛的声音
她们健谈乐不雅观豁达
比我们很多人都活得负责
以是我们改变选题的方向
想要真实呈现这些与我们擦肩而过
但活得明明白白的婆婆的故事
01
口述:魏书珍,77岁,四川仁寿人
创造地:科华北路天桥。
我是在一个雨天把稳到魏书珍(音)婆婆的。
细细的雨避过天桥把四周淋湿,而天桥与人行道交汇处则形成一个没有风雨的小小天下。
婆婆躲在这个小天下里,
经营着自己的小百货摊儿:
地上的油纸布上整洁摆放着鞋垫、松紧带、塑料头花、锁针、指甲刀等小百货。
婆婆坐在随身带的折叠小板凳上,眯着眼穿针,膝上放着一双还未落成的鞋垫。
一瞬间,想起自己的外婆。
那天,也便是打量了一眼我便走了。
第二天,天晴了,但气温仍旧很低。
午间,我与朋友
吃过午饭穿过天桥回公司,
刚上台阶便瞥见婆婆。
她该当是刚摆好摊儿,正蹲着用一张小帕子抹着小商品表面塑料袋上的浮尘,抹了后又仔细地把货色摆放整洁。
我走上前想选双鞋垫,
问,婆婆,这鞋垫怎么卖啊。
婆婆缓缓起身,面向我笑颜满面地说
姑娘,这些鞋垫都是我一针一线自己缝的,现在年纪大眼睛花了针脚没那么细了,不贵,12元一双,你要多大码的?
便是这一搭腔,
婆婆开始跟我聊起自己生命的后小半程。
以下为魏书珍婆婆的自述
我有一儿一女
儿子是成都某高校教授
女儿没念什么书
现在靠做小本儿买卖过日子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险些每个家庭都很困难,养两个孩子能保一个上学就非常不错了。
我家也是这样。
儿子读书有天分,越读越有劲儿,一贯念到博士;女儿贪玩成绩不好,读到初中就不想读了。
我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这便是年夜家的命,有的人是带着当博士的命出生的,有的人虽然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,但终年夜了可能只会打零工。
我一贯跟儿子一家住一起,刚开始帮着带孙子、接送孙子上学放学,后来孙子上高中住校了,我就做做饭打扫一下卫生,去年孙子考上了中心民族大学,寒暑假才回家,我彻底地“解放”了。
我是从孙子上高中住校那年开始摆摊儿的,白天儿子媳妇上班不在家,孙子周末才回来,我只须要每天给儿子媳妇做顿晚饭,白天没事闲得民气里发慌。
当时,几个耍得好的姐妹每天到小区里摆龙门阵都提着个包包,我一问才知道他们在纳鞋垫,卖给收鞋垫的人,一双五块。
我开始和姐妹们一起纳鞋垫,
一天算夜概可以纳三双。
后来听说收鞋垫的人拿出去转手一卖就可以卖十多块钱一双,
我以为划不来,干嘛不自己卖呢?
当年,城管管摆摊设点管得挺严的,我每天提个小兜兜带个小板凳在小区附近摆摊,每天就算卖两双,也比以前做四双交给二道贩子划算。
后来,有顾客说你既然都摆摊儿了怎么就只卖鞋垫呢,还不如再去进点其他货一起卖。
我想也是,平时也常有人来问有没有松紧带,有没有锁针之类。
以是,从没去过荷花池的我,自己搭公交车去荷花池小商品市场进了一些松紧带、指甲刀、头绳,还有一些其他的鞋垫来卖。
这样子,我的商品种类多了,
摊摊规模大了,买卖也好了很多。
不过,实在也挣不了什么钱,由于我进货进得很少,老板不会给我批发价,我假如价格卖高了,也没人要,以是,我也就一样赚一两块钱而已。
很多熟人都知道我女儿一贯没事情,在打零工,大家以为我摆摊是为了帮补女儿,但实在不是,我这么大把年纪了,儿孙自有儿孙福,我已经不太在意挣钱不挣钱的事了,我摆摊纯粹是为了我自己。
我家有老年痴呆症遗传病史,
二十多年前,
我父亲63岁时由于老年痴呆症去世,
没过几年,我的两个姑妈也由于老年痴呆症相继离开。
我已经记不得父亲什么时候得的老年痴呆症了,由于这个病是一个逐渐的过程。
这个逐渐是啥样的,我也说不清,
只能回顾起一些细节。
熟年尾月间,我去给父亲送腊肉,同住的侄儿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一边说
姑妈,爷爷彷佛不认识人了,这段韶光每天早上我去喊他起床用饭,他都会说,你是哪个,咋个在我家喃?
那时在屯子,我根本没听说过老年痴呆这个病,还以为是父亲年纪大记性不好了,并没放在心里,还说侄儿打胡乱说。
那天,我还故意问父亲,
爸,你认得到我不?
认得到,你是魏书珍嘛,我的大女子。
父亲当天利落的回答,
让我更加肯定是侄儿想多了。
没过几年,我的大姑妈和小姑妈也由于老年痴呆症去世,她们患病的全体过程和我父亲的病症千篇一律,刚开始是影象力减退,然后是生活不能自理,到后来身体越来越衰弱,直到由于传染某个小病无法掌握而去世亡。
当几个老辈子相继患了老年痴呆后,我儿子开始关注这个病,我也才知道这个病有家族遗传的危险。
乡头人常常说,不怕人受穷,就怕得拐病。
况且这个病还会遗传。
儿子虽然不说,但我知道他很担心我老了也得这个病,我自己心里也非常不屈稳。
但是,担心能有啥用。
我这个人很好强,年轻时齐心专心想供儿女读书摆脱务农的命运,以是,对待这个病,我还是一样的态度。
年夜夫说,
这不是百分百的遗传机率,
也便是说我并不是肯定会得。
以是,这些年来,虽然我年事越来越大,眼睛越来越花,但是我跟得上时期的潮流,我会用微信,我晓得无人驾驶,我懂共享单车,我以为,只要我坚持动手干事儿,我的脑筋就不会坏,心灵手巧嘛。
人实在便是活一个精气神,我还是想跟自己的命运抗争一下,我要在我活着的每一天都空手发迹,不想每天窝在沙发上抓瞌睡儿。
我想,
如果我能再摆十年摊儿,
也就不咋可能得老年痴呆了吧。
02
口述:邹天娥,65岁,四川南部县人
创造地:锦江区美林湾。
公司搬到幸福梅林后
每天上班放工
我都要走一段两边是菜地的小路。
不论酷暑还是寒冬,路两旁的田地里都有老人在忙活,原来以为他们是附近的原住民,后来走的次数多了,人混熟后,才知道他们大多是附近小区里的老人。
老人们由于要给在成都安家的子女带孩子,离开家乡,开始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办法。
这些老人大部分来自屯子,过惯了跟地皮相伴的生活,纵然来到城市,只要附近有地皮可以开垦,他们仍旧想扛起锄头,种一畦表示自己代价的菜地。
邹天娥(音)婆婆是这片菜地开垦者中相对“入驻”较晚的一位,采访那天,成都刚刚下了雨,婆婆在地里收白菜,她愉快地说,自己种的白菜最好吃了,煮的汤都是甜的。
我们一边陪她摘菜,
一边听她讲述自己
“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地皮”的故事。
以下为邹天娥婆婆的自述
来成都之前,
我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南充。
那年儿子考上南充的大学,我送他到学校,陪他办好入学手续后我便自己搭车回了南部县。
之后就再没有走出过这个县城了。
儿子从小到大上学的用度,
都是我和老头目用双手换来的。
我们一家三口有三亩地,
还有几块自留地。
除了田里的作物和蔬菜,
我们还在自家院里养鸡、鸭、兔、猪。
田里和院里的收成所换的钱,
一部分用来生活,一部分拿给儿子上学。
其余,我家院子门前还有一棵核桃树,每年也能掏几百斤核桃拿到镇上去卖。
从肩膀上换到犁筢上,从猪圈里忙到田坝里,挖土、播种、除草、喂猪、打扫鸡圈……
来成都前,我一贯过着这样的日子,
从没想过,自己还会过上另一种生活。
八年前儿子从南充一所小学调到成都,很长一段韶光都住在学校供应的宿舍。
四年前,儿子贷款买了房结了婚生了小孩,由于夫妻俩都是老师,媳妇家的老人正巧要帮她姐姐带孩子,以是,儿子只好开口让我来成都帮忙。
我一口答应了儿子,我知道如果不是确实很困难,他也不会开口。
但来了成都后,
我才创造城市和屯子的生活差别太大了。
一贯以来,老家用的是土灶、煤炭炉,
到儿子家后我要学着用天然气。
学起来倒不难,但我总担心自己没有关好天然气导致泄露发生失火,常常我抱着孙子走到小区里又折回家检讨是否关好了煤气。
儿子担心我操作不当引起事件,常常提醒我,千万要关好哦,天然气泄露随意马虎导致失火。
儿子念得越多,我心里就越不踏实。
媳妇儿很讲究,
孙子用的统统物件都要消毒。
我理解现在年轻人的不雅观念跟我们老年人不一样,但我比较怄气的是
每次我把孙子的奶瓶儿、奶嘴儿、勺子用开水煮了消毒了
媳妇儿还不放心,非要自己再烫一遍。
有次,
我还看到媳妇
偷偷拿开水烫孙子的亵服,
而我已经洗好并消了毒。
媳妇可能是以为乡下老太婆卫生事情达不到她的标准,我理解,但心里很不好受。
去年孙子上幼儿园了,我提出要回老家,但儿子媳妇说还是希望我连续留在成都帮着接送孙子,还说要把老头目也接到成都来住。
说真的
谁不愿意一家人
在一起享受明日亲之乐呢
以是我也就答应了。
孙子在小区附近上幼儿园,早上八点二十送到园,下午五点二十去接,中间有八小时旁边韶光我都是空闲的。
带了三年孙,和小区里其他婆婆们也混熟了,她们有的来成都韶光长,哪里好耍哪里买东西实惠到哪里怎么坐车都知道。
我随着她们去坐了地铁、看了天府广场、逛了公民公园,还知道十陵有个市场,逢场有菜秧苗卖,也算涨了见识。
小区不远处有一大片空地,是小区方案的配套绿地,但由于建楼,很长一段韶光这片空地都堆满了垃圾和建渣,后来业主们哀求整治环境,物管才逐渐进行了清理。
之后,小区很多老人
开始用石头、树枝栅栏“圈地”,
把地开垦出来种菜。
我到成都来的那年就动了开地种菜的心思,但由于要带孩子顾不上,现在总算有韶光了。
空地已经被圈得差不多了
我找了几圈,才创造两块
被开垦好的菜地间有一块
堆满了石块、砖头的空地。
很明显,大家都放弃了这块地。
我想前想后,还是决定把这块地开出来。
一来自己种的菜吃着放心,二明天将来间那么长的韶光我也有了丁宁的办法。
我花了三天韶光
把空地里的石头砖块
捡到田边,铺成小路。
然后向小区里一个熟习的
老姐妹借了把锄头,开始挖地。
地里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砖头,我又花了一天韶光把砖头清理干净。
由于长期没有耕种,
这块地非常板实,
一挖便是一坨土块,还得用锄头敲碎。
之后我专门焐了肥料浇到地里。
我花了很多韶光培治这块菜地,但第一批种出来的土豆很不尽人意,差不多都是小土豆蛋蛋。
实在,种这块地花的精力与得到的收成很不成正比:
空地附近没有沟渠,没水浇菜,我用菜油桶做水桶,木棍做扁担,隔天就要从家里跑上跑下担十多趟水才能勉强把菜浇透,而夏天就须要每天浇水,早上六点过起床开始浇水,要浇到上午十一点,每天热得全身大汗。
这两年来,我把大部分空闲韶光都用来种地了。
刚开始儿子媳妇不理解,以为费那么大劲儿也没收几窝菜,怕我太劳累。
但他们看我种地的这两年里,不但身体好了,人也爽朗了,也就不再说什么。
有时周末儿子媳妇
要带孙子外出玩,
我一样平常都不去,
我甘心一整天都呆在地里。
累了就坐在田坎边儿安歇一下,和阁下干活的老头老太婆摆摆龙门阵,饿了渴了就吃随身带的干粮和水。
冬天我也喜好到地里忙活,比起窝在家里烤火看电视,我更乐意挥起锄头挖会儿地,浑身热热活活,点都不以为冷。
这跟以前在老家的生活很像,
不用担心煤气是否关好,
心里很踏实很安然。
我便是一个普通的农人,
离开了地皮,我就什么也不是了。
就算来到城里生活,
我还是希望能尽力过上之前的生活,
这是一种念想吧。
03
口述:郭兰英,70岁,湖北人
创造地:三官堂街(成仁公交站)。
如果要说食品给人的印象
那么凉虾是属于夏天的
而顶顶糕便是冬天的景致。
傍晚时分,薄暮的光影中,一个人在街上踽踽独行,或是和爱人、朋友结伴而行,碰着一个冒着热气卖顶顶糕的小车,稍停少焉,就能在寒风中感想熏染到一种甜美的温暖。
当我们找寻到三官堂街的时候
远远便看到公交站背后蒸汽腾腾
走近一看
惊喜地创造一位卖顶顶糕的婆婆。
我们凑到跟前买了一份
自然而然地跟婆婆拉起了家常。
72岁的婆婆郭兰英(音)是湖北人
2010年,郭婆婆因着儿子定居成都便来到当地,每天带带孙子、做做饭、打扫打扫卫生,日子也过得非常充足。
提及卖顶顶糕的缘故原由
郭兰英说
肯定不是由于爱好
也不尽然是为了贴补生活
仅仅是为了一份对子女的疼爱。
以下为郭兰英婆婆的自述
我只有一个儿子,当我逐渐年迈后,我开始感想熏染到他的压力,既要事情,养孩子,还要照顾两边的老人。
以是
我主动来到他安家的成都,
想为他们的小家庭出点力。
当国家二胎政策放开后,我便鼓励儿子儿媳再生一个孩子,我考虑的是,等他们年迈后,有两个孩子分着照顾老人,压力不会太大,而且两个孩子相互有个照料,也是一份人间间的温暖。
儿子的老二出生后,我卖力帮小夫妻带孩子,这个阶段虽然累点,但经济上还能承受。
自从老二开始上幼儿园之后,
我明显觉得到儿子媳妇肩上的压力。
儿子媳妇都是公务员,两人属于工薪阶层,收入一样平常,但也能包袱起一个孩子在成都上学和校外辅导的用度。
大孙子从幼儿园阶段便开始学钢琴和架子鼓,每个月的花费大概是1600元旁边,加上老二上私立幼儿园的用度,压力真的蛮大的。
而且,老二再大一些,也要考虑学一样兴趣,不可能老大学了老二不学吧,这又是一笔用度。
之前我也是干焦急,我的退休费一个月也就两千旁边,就算全部拿出来,也顶不上太大用途,况且,我还有自己的人情光滑油滑,总还有一些费钱的地方。
一次,我在家附近转悠时瞥见有个婆婆都八十多岁了还在纳鞋底来卖,我很受启示,想着自己也可以靠手艺赚点钱嘛。
顶顶糕是我们湖北的特色小吃,我来了成都这么些年,也去过一些地方,我看过卖蛋烘糕、粽子、肉夹馍、手抓饼什么的,但从没见过卖顶顶糕。
以是,我决定自己做顶顶糕
出来摆个摊贴赚点钱补家用。
为了照顾儿子媳妇的感想熏染,我没有见告他们真话,只说自己白天太无聊,想找点事儿做。
做顶顶糕比较费事儿,要把大米、糯米碾成粉子,为了顾客能快速吃到糕,头天晚上我便开始蒸粉子。
白天送孩子上幼儿园后,我得出去买菜,中午大略对付一顿后,大概一点旁边我就推着摊车来到成仁公交站。
算起来,我摆摊的韶光就两个多小时,由于下午三点半我就要收摊,然后去小学接大孙子。
景象好的时候,晚饭后我还会出来摆一下子摊,这时人流量比下午多一些,买卖反倒要好一些。
撤除本钱,我摆摊三天赚的钱,可以给大孙子交一节钢琴课的钱。
以是
虽然每天下午摆摊
要站三个小时旁边
有时也会腰杆疼
但想到儿子媳妇
压力减少了一些
我也以为非常值得。
04
口述:张芝兰,71岁,四川龙泉人
创造地:龙舟南街。
一看到这个街边小摊
从小在屯子终年夜的我激动地扑了过去。
夏姑草、薄荷、金钱草
车前草、地丁、洋姜……
我如数家珍般念叨起这些草药的名字来。摊主是个头戴鸭舌帽的老婆婆,帽子上带绣着“东山花节”字样,有点莫名的喜感。
婆婆很惊异,说,耶,想不到一个年轻人认识这么多草药,不错哦!
就这样,作为有缘人
我和婆婆在街边聊上了
知道婆婆叫张芝兰(音)
来自龙泉
每周隔天便来这条街卖草药
由于公交车可以直达。
以下为张芝兰婆婆的自述
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了,我还是住在龙泉阳光城老屋子里。
屋子前后都有地皮,不远处还有龙泉山。从个人便跟父母到山上拔草药、找野味儿,我理解每个时令山里的出产,知道哪些值钱,哪些罕有。
几十年来,我都是这样生活的。虽然现在条件改进了,环境也变了,但是一到某个节气,我身体里就像有个闹钟一样平常,会提醒着我该上山去采某种草药了。
我会以为,如果我不去采,
它们就白白长出来了。
这样一想,我就心痒痒的,
忍不住要到山上去忙活。
采来的野菜草药太多,我自己也没法花费,以是还是想拿到街上去卖。
但龙泉街上摆摊卖野药的人太多了,为了第二天有摊子摆,大家下午就要到街上占位子,小板凳、一块砖或者油纸布就成。
我家离街太远,每次都占不到位置,以是干脆坐公交车到成都来摆摊。
我的孩子们自己的生活都过得挺好,他们不准我摆摊,说妈你缺钱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,哪里须要那么辛劳地到山上去采草药还要天远地远拿到成都来卖。
但我并是为了钱,几十年的习气没法改变,况且,现在大城市里,人们想找一味什么草药也很难。
我拿来卖也算给大家行个方便,有缘的人碰到我,能买到草药,清个火、祛个毒啥的,也很好嘛
在每个受访的
婆婆身上
我们感想熏染最深的一点是
她们清晰地知道自己
在当下这个阶段里
最想要的是什么
并不遗余力地努力着
纵然已经年迈
知道
自己想要什么
并为之付出
这是
每个社会人
应有的状态
愿我们都能如此
第001期
策划 / 《慢发展》杂志编辑部
采访 | 编辑 / 八哥 以陌叔叔
校审 / 八爪鱼
拍照 / 八哥 以陌叔叔
视觉 | 排版 / 以陌叔叔
主编 / 八爪鱼
音乐 / Andrew Fitzgerald - In the Distance
互助 | 商务 / WeChat: symblo
我们做朋友吧。
















